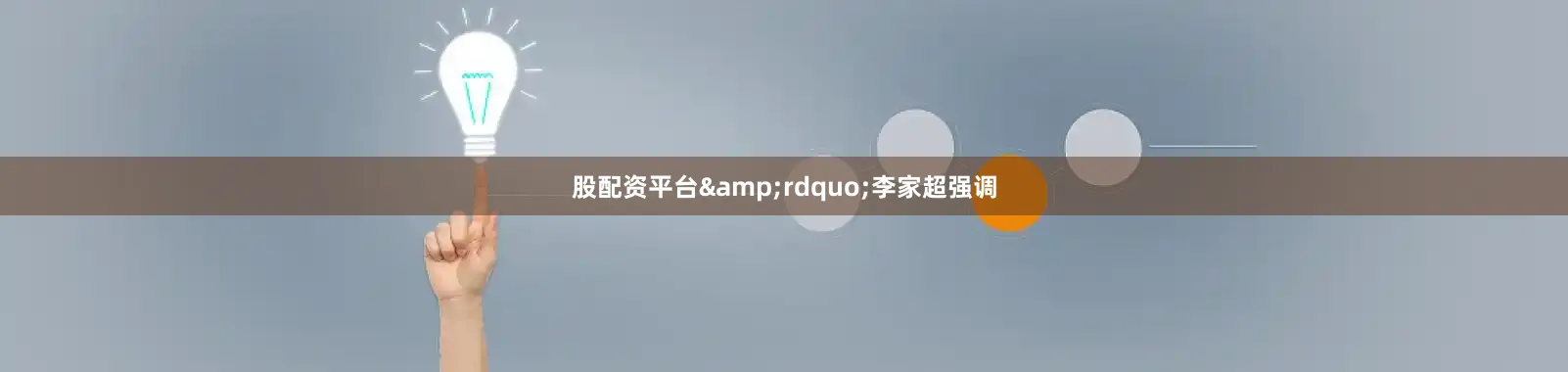在1949年初的那个春天,全国的解放进程已然进入尾声。彼时,中央军委完成了对全国解放军的整编,四大野战军的旗帜在各自的作战区域内高高飘扬。国民党军队的精锐力量,早在三大战役的硝烟中灰飞烟灭,因此,各条战线的推进速度,常被形容为摧枯拉朽,势如破竹,甚至传檄而定。然而,就在这全面胜利的宏大叙事下,第三野战军,这支曾以渡江战役中“没放一枪”的顺利进展而自豪的部队,却在收官阶段的上海,遭遇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挫折。
尤其是在月浦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镇,三野不仅未显尽全胜之势,反而在拥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,兵折数阵,甚至可以说是一次“阴沟翻船”。两千多名忠勇的战士,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倒下,其中一个主攻团,竟然打得只剩下区区62人。这与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形成强烈反差,不禁令人扼腕长叹。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,让一支本该势如破竹的军队,付出了如此沉重的牺牲?
大局已定,何来重创?

当时的局面,南京已经解放,上海成为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块“孤岛”。军事上,上海的战略意义几乎为零。三野的态势是,第七兵团驻扎杭州,第八兵团在南京,第九兵团位于松江,而叶飞率领的第十兵团则部署在苏锡常地区。面对这样的兵力部署,上海的国民党守军多是战场上溃败下来的残兵败将,建制不完整,武器装备也显不足,早已是惊弓之鸟。
然而,蒋介石却另有图谋。他坚决要求死守上海。首先,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,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据点,蒋介石妄图在此开战,试图将美国拖入其中,进而引发他心心念念的第三次世界大战。其次,上海是中国财富的集中地,大量黄金白银储藏在银行仓库,这些都是他反攻倒算的“救命钱”。为此,蒋介石任命亲信汤恩伯指挥二十万大军据守上海,并利用日寇遗留的永久性工事,妄图坚守六个月。
高层算盘,前线苦涩
经历了约一个月的休整,三野开始着手制定“战上海”的计划。副司令员粟裕亲自部署,决定以叶飞的第十兵团(欠一个军)作为西路军,主攻吴淞,同时将原属第十兵团的31军划归第九兵团指挥。第九兵团则作为东路军。总体策略是先切断敌人的海上退路,然后“关门打狗”,确保敌人无一漏网。

计划中,对第十兵团的时间要求异常苛刻:5月12日出发,5月14日拂晓前必须抵达吴淞。叶飞接到电报后,站在地图前反复丈量,从常熟到吴淞的距离超过120公里,途中还横亘着浏河,并且要经过嘉定、月浦、杨行、刘行等国民党军重点防守区域。即使是强行军,一天最多也只能跑六七十公里,更何况还要打仗、渡河。叶飞对此深感忧虑,他想不通粟裕为何会设定如此紧迫的时限,难道是轻信了情报,认为敌军会起义,所以不会有硬仗可打?
叶飞带着满腹疑问,打电话给在苏州总部的粟裕,随后立即前往面谈。他坦率地表达了对西线兵团作战方案的困惑:“我们距离目的地大约120公里,汤恩伯的部队又在我们要路过的地方部署了太多兵力。两天内到达吴淞,会有太多困难。”他还一个一个地指出地图上那些敌军重点把守的永久性工事,强调“2天时间肯定到不了啊!”
粟裕耐心听完,解释说:“根据中央提供的情报,上海守敌和平起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,如果谈成了,从常熟到吴淞口就不会有什么大仗,所以,野战军命令10兵团采取猛插战术,分割包围,限两天到达困难自然会有,但不是不可行。”他还笑着对叶飞说:“就是因为有困难,才会让你叶飞上嘛。”接着,他又提到,29军军长胡炳云专门找他,希望能捞个仗打,觉得这次对29军来说,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。

叶飞听闻29军主动请缨,心里反而更没底了,他再次表达担忧:“月浦、浏河一带是汤恩伯重点防守地区,我担心29军经验不足啊!”但粟裕态度坚决,他强调:“我说了,上海守敌可能部分起义。我和张震参谋长考虑到各方面因素,认为你部必须完成任务。记住,赶到上海就是胜利。”叶飞虽然嘴上答应了,但心里却仍在打鼓,他隐隐觉得,粟裕这次或许犯了个兵家大忌。
渡江以来,三野上下弥漫着一股浮躁气息,部队进展过于顺利,国民党军或投降、或起义、或逃跑,极少组织起有力的抵抗。军中甚至流传着“渡江渡江,没放一枪,追击追击,不堪一击”的顺口溜。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,导致我军对敌情判断失误,认为汤恩伯这个“草包”不足为虑。
而事实上,国民党早已吸取教训,在军内进行了残酷的“大清洗”,汤恩伯甚至“卖友求荣”逮捕并导致陈仪被杀,因此上海守军从一开始就不存在起义的可能。然而,粟裕却一直以敌军会起义为前提制定作战计划,将这场战役视为“接收”,而非一场实实在在的战斗。

这种过于乐观的判断,直接导致了第十兵团两天内抵达吴淞的超高要求。我军以步兵为主,缺乏牵引车辆,如此快速的行军,重武器必然滞后,难以应对敌人坚固的工事,这正是兵家大忌:料敌必从严,而这一次,粟裕确实轻敌了。
月浦绞肉机
在第十兵团的必经之地月浦,汤恩伯早已做足准备。他督促士兵修建了星罗棋布的子母堡群,各堡垒间交通壕相连,壕沟内甚至可行驶吉普车,电网和鹿砦层层叠叠。所有房屋、围墙、工厂都被改造为抵抗重点。蒋经国视察后,将此地比作“东方的斯大林格勒”。
更棘手的是,驻守月浦的国民党守军是刘玉章带领的第52军,这支老牌中央军被誉为“第六大主力”,拥有强大的作战实力,是少数敢于与我军拼刺刀的部队。辽沈战役时,它更是东北五十多万国军中唯一一支保持建制逃脱的部队。现在,毛泽东曾一度忧虑的这支部队,成了现实的威胁。

月浦镇,作为进入宝山、吴淞的唯一门户,地形易守难攻。叶飞将这个艰巨任务交给了29军87师260团。攻击开始前,260团上下都充满兴奋,毕竟解放战争已近尾声,这是立功评奖的最后机会。由于太过急切,团部指挥官对月浦的敌情、地形和工事了解不足,以为敌人会望风而逃。但这一次,敌人选择了顽抗。
战斗打响后,260团各部一马当先,对敌人防御工事进行强攻。然而作为主攻团,他们仅有3门山炮作为支援,其他重炮还在后面赶路。当官兵们逼近敌人工事时,猛然察觉不对劲——敌人的火力过于猛烈。
52军在月浦前沿阵地布置了一个团,宝山、吴淞一线更有12个炮兵团,几百门火炮,长江上还有30多艘战船可向岸上开炮,附近的龙华机场更有大量国民党军飞机前来轰炸。在敌人海陆空立体反击下,团政委萧卡果断决定,立即改变猛插战术,就地修筑火力点,挖掘战壕。

相比之下,负责助攻的253团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在奔袭月浦途中,他们从俘虏口中得知月浦“没什么坚固工事”,便仍按原定计划猛插吴淞。晚上,团长带领众将士在一处“坟场”休息,不料次日清晨才惊觉,那些一个个“坟包”,分明是国民党军的碉堡。团长立即命令士兵找掩护,却已来不及,国民党守军一齐开火,大批指战员倒在血泊之中。
5月13日上午,260团经历了残酷的考验。作为主攻团,他们只能蜷缩在刚刚挖好的战壕里。国民党军困兽犹斗,炮弹不断从空中、江面和对面的炮管中倾泻而来,260团各部伤亡惨重。其中,主攻1营还未开始进攻,损失就达到了三分之一,营长和副营长都身负重伤。
无奈之下,260团改变战术,采取多路小部队攻坚战术,用小部队多路摧毁堡垒群,二梯队向纵深突击。然而战术的改编,并不能限制敌人炮火的威力。在冲锋的路上,260团和前来助阵的253团伤亡累累,战士们前赴后继地倒在敌人密集的交叉火力之下。

在如此绝境之中,260团的战士们迸发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。进亦牺牲,退亦牺牲,不如为了人民轰轰烈烈地牺牲。他们呐喊着口号,前进再前进,冲锋再冲锋,含泪踏着战友们的尸体,接近敌人的堡垒,然后用炸药包、土飞机将敌人连人带堡送上天。
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冲锋,260团终于攻克敌人在月浦的前沿阵地,第52军25师因为伤亡惨重,只好退守于街区之内。勇士们见敌人溃逃,如猛虎入羊群般追击。
在追至月浦镇时,战士们面前出现一条浅浅的小河。战士们并未在意,皆提起裤腿涉水而过。然而就在这时,隐蔽在草堆、树林和坟包中的国民党地堡群突然开火,我军既无遮蔽,又无重武器支援,不断有战士被密集的火力扫倒。
但在死亡面前,战士们仍未停止前进的脚步。夹在部队中的萧卡看着不断发起集团冲锋的战士们,急在眼里、痛在心里,他不断呼喊战士们先撤退。

但战场噪音太大,根本无法制止,只好跟着战士们一起向前冲。经过一番血战,260团终于在5月14日黎明到达敌人阵地前沿。萧卡在战壕内清点部队,竟然只找到步兵120多人,干部更少。在一个被占领的碉堡内,团警卫班还发现几个伤员正和几个国民党伤员对坐在那里,互不相犯。
此时的260团已是强弩之末,再也无力攻击。就在这时,军长胡炳云打来电话:“你们260团还能打吗?”萧卡回答:“我们距离敌指挥部只有50米了,还能打。”胡炳云一听大喜:“那太好了,你们继续担任主攻,我调259团的两个营支援你们,还是由你们主攻。”在259团的支援下,260团仅存的120多名步兵对敌人发起了猛冲。狭路相逢勇者胜,敌人终于抵挡不住我军凌厉的攻势,被迫撤出了月浦镇。
听闻月浦解放的消息,胡炳云激动得不住颤抖,他告诉260团副团长梅永熙:“老梅啊,你们打得好,虽然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,但最终还是赢得了胜利,你们260团打得好啊!军党委准备向兵团打报告,给你们请功。”然而,我军攻占月浦后,国民党军不甘失败,立即展开反攻。5月14日夜里,萧卡和梅永熙带领战士们奋勇作战,不断打退敌人。后来清点人数,260团仅剩的120多名步兵,如今只剩了62人。

敌人在舰炮和坦克的支援下,仍持续不断地对我军展开疯狂进攻,260团和259团渐渐不支。就在这时,258团的一个营突然进入了月浦。原来在混战中,这个营与团部失去了联系,被炮火声吸引,找到了战场。有了这支生力军,我军最终打退了敌人的反击。我军虽获胜利,但牺牲依然惨重。259团团长胡文杰在前沿指挥时,不幸被敌舰炮冲击波波及,胸口被炸开一个巨大的洞,不幸牺牲,成为上海战役中我军牺牲职位最高的将领。
代价昂贵,幡然醒悟
在整个月浦战役中,第十兵团的28军、29军在月浦、刘行、杨行与敌52军激战,付出了2000人的牺牲。新中国即将成立,全国即将解放,这些三野的精锐战士却倒在了黎明之前。其中260团几乎被打光,干部伤亡惨重,团参谋长李仲英负伤,12名营级干部有11名负伤。
当粟裕从叶飞那里得知第十兵团遭遇惨重伤亡之后,也立即改变了战术。他将此前的“猛冲战术”变更为“近迫作业”,尽管每天只能前进两到三公里,但伤亡却大大减少。到了5月23日,第十兵团终于攻克了吴淞,但这一天,比原定计划足足迟了9天。为了不打烂上海,我军在攻击过程中也没有使用重炮,这也导致了攻击速度的大大减缓。

正是由于我军战术的调整和时间的拖延,汤恩伯得以将第52军、54军、75军等部装船打包,满载金银和美钞,从海上逃向了舟山。而那些被留在岸上的15万3千国民党军,则成了我军的俘虏。
月浦战役,无疑是一场血战,也是一场代价极其惨重的“惨胜”。此战之中,国民党52军及其军长刘玉章大出风头,战后还被蒋介石授予勋章。到了台湾,52军更是成为了台军的绝对主力,即使到今天亦如此。因此,月浦战役的战略目标并没有全部达成,还是让部分国民党军精锐逃跑了。
谁都会犯错,即使身经百战的粟裕也难以免俗。这场战役给解放军留下了宝贵的教训:将不明,则三军大倾;将不精微,则三军失其机。料敌必从严,轻敌乃兵家之大忌。正是月浦之战的惨痛教训,促使解放军在后续的军事行动中更加谨慎,也为后来金门之战的失利,埋下了更深层次的思考。

牺牲,是为了什么?
月浦之战中,第29军展现了其适应极端战场条件的能力和战术灵活性。尽管起初并非主力部队,但在关键时刻,他们成功应对了挑战,保持了前线稳固,逐步推动了整个战局向有利于解放军的方向发展。
叶飞司令员在收到战报的那一刻,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,愤怒地拍打着桌面,对着兵团司令大声喝问:“这算什么胜利?这不过是用士兵的生命堆砌的所谓胜利!”他的声音中满是对这种惨烈代价的不满和痛苦。
是的,战争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胜利者。每一次所谓的胜利,背后都隐藏着无数的牺牲和深深的悲伤。月浦之战虽然在历史书页上记录为一次胜利,但它也展示了战争的残酷和不公。在那场战斗中,260团的士兵们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勇气和坚韧,他们几乎以赴死的决心,守护每一寸土地,直到最后只剩下62人仍能站立。

解放上海后,29军指挥官胡炳云将军对260团的英勇表现给予了高度赞扬。他在部队表彰大会上特别提到260团的出色表现,称其为“全军的楷模”,并强调了他们“打得好,打得顽强”的战斗精神。这份赞誉是对260团士兵无畏精神的认可,也是对他们牺牲和努力的高度肯定。
尽管过去已逾70年,但260团战士们的英雄行为依然值得我们铭记和传颂。他们是战场上的勇士,更是我们心中的英雄。他们的牺牲提醒我们,和平的价值远超过任何战争的胜利。
盛达优配app-正规配资平台app-在线炒股配资门户网-证监会允许的配资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